尹稚:“半城市化”不是健康的城市化
來源:中華建筑報 時間:2012-06-26 12:12:32 [報告錯誤] [收藏] [打印]
采訪對象: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尹稚

尹稚:“半城市化”不是健康的城市化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以城鄉二元分治結構的長期堅守,人為制造城鄉阻隔,導致物質空間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脫節。
▲社會問題頻生的真正原因在我們選擇財富積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們為何一定要剝削一部分人才能讓另一部分人富起來?
▲我們將在戰爭年代的管理軍事系統的經驗放大到了全社會系統中,即使是在農業社會,也不可取。
今年的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人口已經超過總人口數的50%。城市化作為一個關乎城市發展未來、國家發展未來的問題,涉及經濟、思想、政治、社會等各個方面,中國并不是第一個走上城市化道路的國家,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卻是全人類歷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一次人口遷移,城鄉二元化的制度設計注定了在這一過程中,有些人會成為時代中最為失落的人群。這一正在發展變化著的歷史能夠獲得個人視角的何種解讀?筆者采訪了北京清華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尹稚教授。
記者:目前,在一些偏遠村落,留守兒童正在呈現出低齡化的趨勢。在一些村小學,出現了一個年級100%留守兒童的現象,偏遠地區基層社會在兒童安全、公共衛生和教育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如果不進行改善,兒童在成年后可能還會延續其父輩的命運。您對此如何看待?
尹稚:之所以中國有大量留守兒童的出現,是中國“半截子城市化”現象造成的。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半截子城市化”進程,從物質環境建設看,高樓大廈的拔地而起讓人產生一種幻覺,似乎中國與發達國家已無區別,但從人口遷移角度看其實有根本性區別。
從全球范圍內看,各地域的城市化都是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和角色轉換中完成的,國際上稱這類遷移人口為new-comer(新移民),而在城市規劃、城市社會學的研究和城市建設實踐中,最主要的關注是,這些新移民如何以比較低的門檻進入城市,能夠在城市中隨著就業形式的轉換,實現財富的積累,完成生活方式的變化,實現從“農民”到“市民”的代際轉換。這個過程不僅僅是城市建設規模擴張、建設形態日益立體化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人的生活環境改善、可享受的公共服務水平提高、人口素質不斷提升的過程,是人的現代化過程。而這一過程會通過城鄉互通最終惠及全體國民,實現民族振興。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以城鄉二元分治結構的長期堅守人為制造城鄉阻隔,不斷遲滯重建城與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資源流動的正常途徑,導致物質空間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脫節,形成所謂“半截子”城市化現象。
在1949年后,中國的工業化積累并沒有完成,又遠離了資源外掠奪的時代,這些原始積累在哪些人身上獲得?政府第一個看到的是農業中農副產品的剩余價值,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統購統銷開始,社會把農副產品上榨取的剩余價值轉移到工業化的財富積累中來,史稱“剪刀差”。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工業化的積累進程和城市化進程重疊,城市對農村的掠奪又多了兩重含義——“農民工”和“農村勞動集體所有制”的土地。
一方面,我們創造了一個非常糟糕的詞語“農民工”,這個詞本身帶有非常強烈的社會和政治歧視色彩。用一種“農民工”不算人的態度榨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創造紅利。另一方面更為徹底,中國爆發式的城市化進程及其財富積累很大程度上以土地作價獲得,城市政府將農村的土地以幾十、幾百元一畝的價錢拿來,翻整后直接投入市場,獲取數倍至數十倍的利益。“剪刀”從一把變成了三把,基本剪掉了農業人口的生活轉型的可能,正常的、勤勞致富的農民日益變成赤裸裸的流動貧民,除了自己的體力、血汗和手藝,不擁有任何可靠的生產資料,甚至失去家園。
鄉村人常年在外打工,又不能在城市定居,在此之初引發了春運、欠發工資和醫療保障等社會問題。這是“農民工”當代人的問題,20年前對“農民工”的歧視甚至體現在統計數據上,他們創造的產值歸城市,但在統計人均GDP等各種人均指標時,農民工不計入城市人口基數。很多城市在數據上呈現出非常假象的繁榮,如果將打工人員全部加入,其數據值至少減少一半。這些是社會各界最早呼吁的問題,而在現階段,由于半城市化的現狀,新的焦點再度爆發。進入城市打工的原鄉村居民的就業形態早已轉換,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后,其后代已經進入早教、入學甚至是高考年齡,而歧視政策依舊,當代人的問題演化成代際交替,事關子孫后代的問題,這一現象正是歷史走到今天的必然。
記者:您認為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應從何入手?
尹稚:第一,要逐漸廢除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讓鄉村居民自主選擇居住地和就業地。中國古代的戶籍制度不是城鄉割裂的,是將城鄉看作“一盤棋”的正常管理思路,與我們今天的城鄉分割不同。基本上,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重點并不在農村,鄉村的承載力是有限的,重點在城市。我們要重新打破城鄉之間的墻壁,如果對鄉村居民的歧視政策不改,這個問題將永遠存在。從政治上講,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是政府在執政中越來越不相信人民。在改革開放初期,面對嚴重的失業問題,面對整體的公共服務和資金儲備不足的問題,通過落實政策,實現了居民自主就業和個體經濟的繁榮,出現過多贏的局面。但在近十年,改革開放初期的自下而上的活力都被拋棄,全部問題被納入到自上而下的體系中去處理,規劃界有句名言“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 Maybe it’s nothing” ,套用過來可以講“政府萬能,實際會走向政府無能”,造成社會問題頻出,政府實際上要承認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打開壁壘,讓民眾發揮才智去解決問題是第一步。
這當然會有阻力,真正的阻力是通過這種制度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在過去30年高速擴張中實現了非常瘋狂的原始積累,在現階段經濟增長適度放緩的過程中,應該利用機會重新安排分配。健康的城市化說到底是一個合理分配財富的問題,針對必將進入城市,并參與城市財富創造的新移民,如果不重新調整分配原則,做出公正公平的安排,所謂的城市化對人而言也就沒有實質性的意義。
第二,要切實維持進城門檻的低標準,不要盲目抬高進城成本。為什么全球很多城市都會出現“貧民窟”這種問題?因為所有的城市的新移民在開始轉換生活模式時都沒有財富積累,都會選擇最廉價的方式進入城市,但只要能住下來,通過若干年的努力就有機會實現家庭生活條件的改善。中國為何沒有出現這種類型的“貧民窟”?中國在歷史建設中遺留了很多城中村,在大都會地區存在大量未利用的地下空間,其取代了其他國家的“貧民窟”,為新移民提供了廉價但同樣條件惡劣的居住場所,大幅度地降低了這些人進入城市生活的門檻。但我們沒有反思對這一大規模群體的虐待,在制度化出路尚未建立時,就要將城中村全部掃光,將地下室清空,這其實是更不人道的做法,是將制度以外的遷移渠道和定居的可能渠道清理掉的思路,這不是正常的實現城市化進程的思路。
記者: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否存在模式單一化的問題?應如何使城市化進程更有活力?有學者認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缺少經驗,您如何看?
尹稚:一場城市化進程一般包含兩個方面,一個是自上而下,一個是自下而上,我們在學術層面上稱此為他組織過程和自組織過程。從全球城市化進程來看,他組織過程是長遠的、宏觀的,大系統的規劃建造過程,決定了城市的基本框架和結構;而在其中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社區乃至每一個個體如何生存、如何調試、如何創造出城市的繁榮是一個自組織過程。
在改革開放初期20年,中國進行過很多探索,開始有自組織現象的出現,并已經在探討小政府、大社會的形態,但是這十年是真正做成了龐大無比的政府和對基層社會的全面的摧毀。舉例來說,近幾年經常出現各地城管與商販之間的沖突不快。城管針對的不是體系經濟,而是非體系化的自然經濟。哪怕在再發達的國家,小商販的小本經營也是存在的。因為微觀細胞的相關作用沒辦法完全納入到體系經濟中,恰是這種形態的存在補充了體系經濟的不足,能夠讓經濟運轉得更和諧、更有活力。
“社區”同樣應對的是社會的自組織過程。在中國皇權社會,有“皇權不下鄉”的說法。因為這對執政資源的消耗非常大,稅收和國家預算無法支撐,如果硬要支撐,必然加大對人民的掠奪,這是在“維穩”和“激發民變”之間的明智選擇。封建社會主要通過基層的鄉規民約,以文化、道德引導的過程實現社區穩定。歐美國家的政府不同黨派之間的分歧和博弈對社區的直接影響也是有限的,社區層面的社會狀態實際上帶有很強自治性。一方水土一方人,大家達成共識,慢慢形成五花八門的組織以維持社會基本安定。而近年來中國政府將其末端神經深入社區,以“支部建在連上”的軍隊管理模式進行公共管理。軍隊是簡單系統,但是社會是復雜系統,我們將在戰爭年代的管理軍事系統的經驗放大到了全社會系統中,即使是農業社會,也不可取。
我們的政府一直有對抗性的思維慣性,認為自己戰無不勝,不僅戰勝階級敵人、戰勝大自然,還可以戰勝歷史規律;而一部分技術官僚、專家學者迷戀于技術至上的問題思維,認為所有的問題都能通過清晰的邏輯解決。任何復雜系統都可以有調控,包括前饋性調控和反饋性調控。如果從科學的角度講,前饋性調控因其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難以實現精準預估,存在局限性,適合控制復雜系統的宏觀層面,越具體,越細節,越不靠譜。市場體制以反饋性體系為主,在越小尺度中實現越有效,用于宏觀控制則代價非常大,有時根據反饋進行宏觀調整時難度極大。從全球看,大部分地區國家都在走混合型道路,既有前饋控制,也有反饋控制。
近十年,在中國經濟、人文環境剛剛有所改善的情況下,政府突然沒有任何節制地加大他組織進程,而這一他組織進程并非基于價值觀和政治觀的鐵板一塊,在這樣一個時候加大前饋性控制,人們必然質疑改革成果究竟被誰獲得,他組織進程為主的權貴經濟還能走多久。這不是信仰問題,而是關于在制度上應選擇什么路徑才能實現社會全民的整體利益的討論。
記者:目前的全球化因為經濟危機進入到新的階段,但在這個過程中,歐美地區的巨型財團受益最多,在今年爆發的倫敦青年暴動、美國市民占領華爾街活動等也有此因。有經濟學者指出中國未來的城市化應結合經濟轉型而動,也有規劃學者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在路徑依賴中會相對艱難,您如何看其未來?
尹稚:中國的、國外的社會動蕩,基本上是既得利益者的貪婪造成的。歐美國家的政企是剝離的,市民認為受到了資本家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可以打出擁護社會主義的旗號,其國家政府可以用權力調整企業和市民之間的關系,達到再一次的平衡。我們國家缺少市民社會,有民權意識是近年的事情,一直形成不了市民社會集體性的利益訴求;而中國的發展軌跡是政府和市場的高度結合,在經濟危機后,政府積極投資于國有壟斷企業,進一步加大了權力和利益的捆綁,讓社會感覺更絕望。在我國,政府并不是剝離于市場的第三方力量,這導致了真正向企業表示不滿的市民不多,基本上將不滿針對于政府,這是中國特殊發展道路和國情決定的,也和中國的發展階段有關。如果未來要重塑政府形象,政府要從市場圈中脫離出來,打破政府和企業同一訴求的模式。深層次的頂層設計不解決,簡單靠投資和經濟增長平復民怨,是難以解決社會問題的。
社會問題頻生的真正原因在我們選擇財富積累的方式缺乏公平公正性,我們為何一定要剝削一部分人才能讓另一部分人富起來?雖然歷史階段有其被迫性,但走上這條路有非常不明智的一面。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必然有一些人會做出犧牲,但政府在制度設計上不應該以這些人的犧牲作為發展前提,資本的積累不能按照奢侈的方式進行,我們不需要以大量資源的消耗實現城市化發展。
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在不斷擺脫路徑依賴的過程中謀求發展,成功擺脫路徑依賴才會成長。中國的財富積累速度在近30年是全球最快的,但是付出的代價可能也是全世界最多的,而資源代價、環境代價、社會倫理代價是物質不能償還的,這些“后遺癥”需要通過長時間的修正才能慢慢減緩。
目前中國處于高速發展時期,可能要在高速發展時期過后才能有效提煉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理論成果,歐洲城市化轉移的人口不到中國需轉移人口的二分之一,美國更少。如果中國能夠在不爆發大規模劇烈社會沖突、沒有向全世界掠奪資源的前提下完成十幾億人口的城市化,這是對全世界的貢獻,中國政府也將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城市化進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試圖在幾十年內完成城市化進程是不現實的,這是很漫長的積累過程,尤其是人的改變。目前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通過高強度的城市化搭建平臺,市、縣、區、鎮、鄉、村一哄而上,是一個全面的蔓延性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屬于非規范化的發展套路,“亂拳打死老師傅”,導致中國環境事件頻發和社會矛盾激化。正常的城市化現在應該是層次提升或者叫內涵式提升,如果想找到高端經濟行為的良好發展平臺,只能向真正適宜發展城市的地區集中經濟能量,應注重內在要素的提升,上一個臺階。
-
王耀:滿足客戶的客戶需求 才是好作品

面對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建筑裝飾設計企業應該如何應對?作為設計院的領導,如何引導職場新人快速適應崗位
- 張展翼:平衡設計中的邏輯和非邏輯
- 劉亞濱:青春一路狂飆
- 設計師高媛:沒有完美的設計,都有不同的遺憾
- 優秀指導老師專訪 | 從選手到導師 周夢琪的“中裝杯”之路
- 中裝新網專訪 | 蔣燕微:用熱愛,譜寫設計的每個篇章
- 中外建姜靖波:深化設計未來也許更多是經驗和軟件的結合
- 鴻樣設計鄭惠心:創造多方共贏的互動空間
- 南通裝飾設計院秦嶺:成功的設計創意是實現得了的!
- 蔣繆奕:豪宅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
-
什么是設計師的成本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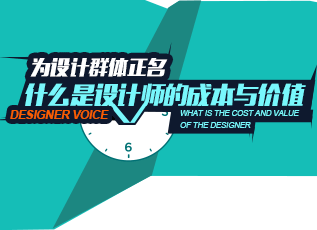
近日,《你個設計師有什么成本?》一文刷爆朋友圈,文中講了一個故事,表達了大眾對成本的理解,也提出了一個有
LINKS
中國室內設計與裝飾網 | designboom設計邦 | 新華網 | 中國建筑新聞網 | 搜房家居網 | 北京市建筑裝飾協會 | 中裝設計培訓 | 鳳凰家居 | 中國建筑與室內設計師網 | 中國網建設頻道 | 筑龍建筑設計網 | 視覺同盟 | 湖南室內設計師協會 | 城視窗 | 中裝協設計網 | 非常設計師網 | 新家優裝 | 行走吧,媒體團! | 新疆室內設計聯盟 | YANG設計集團 | 中式設計 | 大宅國際別墅裝修設計 | 四合茗苑中式裝修 | 設計王DesignWant?&?住宅美學Living&Desig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