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巖松:建筑是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關懷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時間:2018-09-28 11:24:45 [報告錯誤] [收藏] [打印]

馬巖松
“為什么我只會被某一些作品打動?因為它們把我帶到了一個不知何所在的地方,只能自己去感覺,去思想。”
如果說在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的邀約之前,建筑師馬巖松和當代藝術有過什么重要交集,那就是丹麥-冰島藝術家奧拉維爾·埃利亞松(Olafur Eliasson)了。
2003年,埃利亞松在英國泰特現代館(Tate Modern)的渦輪大廳里做了那個氣勢萬丈的人造太陽——“天氣計劃”(the Weather Project)。第一次,置身于一個美術館空間,馬巖松感受到從未有過的觸動。
更奇妙的是,幾年后,他就和這位自己喜歡的藝術家有了一次合作。
2004年,在離開倫敦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建筑事務所后,馬巖松回北京創辦了MAD事務所。這個耶魯生以令人驚訝的速度成長為青年建筑師中醒目的人物。2010年春季,北京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UCCA)邀請馬巖松和埃利亞松跨界打造建筑-藝術展——《感覺即真實》。無論從藝術家的國際影響力還是作品呈現形式,這都算是一個年度藝術事件。當時的報道描述他們在現場制造了一個“另類現實”:馬巖松為展廳設計一個長近60米的蜿蜒空間,埃利亞松用紅、綠、藍三基色組成的“熒光燈陣”以及填充于整個空間的霧氣,構成了一個人工的光譜空間。光譜是虛幻的,體驗是真實的,正是埃利亞松最容易令觀眾興奮的,“將空無一物的巨大空間化為給觀眾帶來神秘體驗的人工環境”。
對于和埃利亞松合作的馬巖松,時任UCCA館長、國際著名策展人羅姆·桑杰斯是這樣介紹的:作為中國建筑界的杰出代表,馬巖松顛覆了業內固有的分類和分級模式。他的作品永遠充滿令人驚喜的元素,以最前沿的科技材料和技術手段,實現其大膽的建筑設計理念,并總能牢牢抓住觀眾的視線。他奔放的建筑形態仿佛有機體和人類實體,傳遞出令人無法抗拒的生命力。
8年以后,現在的馬巖松怎么看待他和埃利亞松的這件作品?“這種東西對我來說也屬于大地藝術的范疇吧,跟自然或者環境結合的作品,做出來氣場就非常大。可能跟我建筑師的身份有關系,我對那種特別具體的、敘事性的東西一直沒什么感覺。”
超現實、大氣場、自然、想象、幻覺、前沿的科技材料和技術手段……在2018年這個夏天的越后妻有,馬巖松把這些概念再次全部用到了隧道作品中,包括埃利亞松式的熒光燈陣和三基色光譜。

馬巖松“光之隧道”系列作品之《天外》
清津隧道建于1996年,有20多年歷史,并不太老,也沒有廢棄。它位于上信越高原國家公園界的清津峽(日本三大峽谷之一),專為步行游覽溪谷而修建。隧道全長750米,受中國古代哲學系統觀“五行”(金木水火土)啟發,MAD在隧道中的每處空間只是加上極簡的一件作品,原有空間卻因此擁有了新的想象和張力。五件作品,既獨立存在又在內部邏輯上呼應彼此,完成一條“光之隧道”(Light Cave)。
“光就是材料。”馬巖松和他MAD的同事們并不糾纏于是在做一個藝術裝置,還是在幫十日町市政府改造一個建筑空間,他覺得這兩者沒有界限,都是在現有條件下去創造,這條件可能是自然環境,也可能是人造環境。“隧道已經在這里,內和外的關系也有了,我們只是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上去做想象。我并沒有特別想藝術應該怎么做。”
第一洞依舊空無一物,保存了原初的樣子。途中有變換三基色的燈光作品“色”被安置在隧道兩壁,引領我們走進“即將發生”。
第二洞《窺》,建筑師對空間功能的敏感顯現了,他們做了一個既是真正衛生間也是裝置作品,使用了一種透視材料,人們“從室內能夠看到室外,外面的人,外面的景色,但是別人看不到你”。被人群圍繞的你,好像隱身了。
第三洞是在洞壁安放了數十個水滴形狀的鏡面,對這件《滴》的作品,馬巖松闡釋為“像在沉悶的水泥墻體上鑿開好多個通往未知空間的洞”。為封閉制造開放的詩意錯覺。馬巖松認同把所有建筑都看作情感行為,是人對自我的認識,以及對自己和世界關系的認識的變化,“要不然怎么從窯洞、帳篷變到現在的建筑?”所以他覺得無論建什么,一座城市還是一個公共空間,都基于人對世界的想象。當然也包括這次的隧道改造。
“光之隧道”盡頭,就是第四洞作品《鏡池》。行至山窮水盡,卻豁然開朗:一片水面將半圓的洞口反射成為一個完整的圓形,似山水畫屏,也似宇宙黑洞。我們可以浸足觀景的那片水面是從清津峽引上來的河水,清涼透骨。洞頂墻壁鋪設的磨砂不銹鋼板,將外面的山水、天空的光線甚至微風吹動的細小水紋都反射到隧道內部,內和外的邊界模糊了,現實和幻覺形成交替。這是整個隧道作品最精彩的末章,由遠而近,每走一步眼前看到的畫面都在變化,而繪畫者其實就是自然本身:陽光、空氣、山風,巖壁、河水,還有人。人流多少對于感受這件作品影響很大。7月29日開幕那天,入洞的人密集,作品疏朗的景深就短暫消失了。
我們和馬巖松采訪對話的地方,是回到洞外的第一件作品《天外》之所在。在深澗之上、進入隧道口必經的路邊,MAD蓋了一個小木頭房子,其大斜坡的屋頂是越后妻有山區特有的建筑形態,因為這里長冬多雪。一層供人小憩,二層閣樓是一個藝術參觀空間,正中一方溫泉泡池,坐在池邊,頭上是屋頂嵌入的圓形凸鏡正將山澗中真實的河流“吸”到空中。低頭踏入現實,仰頭即為幻象,虛虛實實之間,是自然和人工之間的互譯。
把“熟悉”抽離干凈
三聯生活周刊:在接受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的邀請之前,你對“大地藝術”有什么了解?
馬巖松:我看過美國的大地藝術,在內華達山區,詹姆斯·特瑞爾(James Turell)做的那個“Roden Crater”(羅丹火山口)。藝術家上世紀70年代買下兩座有40萬年歷史的死火山,用二三十年時間在死火山口里挖一個隧道洞穴,然后以空間和光線來創造了一件巨大的作品。還有日本的直島,作品是放在自然環境里面的。其實建筑也算是一種大地藝術吧,因為它跟大地和環境都有關系。
但大部分藝術作品還是放在一個空間里展示的。我發現,我個人對美術館空間里面的藝術特別沒有感覺,不管是繪畫還是雕塑、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可能是我對一件作品所存在的時空特別敏感吧。我真正被空間里的作品打動是為奧拉維爾·埃利亞松,2003年他在英國泰特現代館做了一個“天氣計劃”,就是那個大“太陽”。那年我剛畢業,在倫敦為扎哈工作。在學校的時候我就覺得埃利亞松的東西很牛,所以那次專門去看了展覽,就非常被那種氣氛觸動。
三聯生活周刊:第一次走進大地祭這個隧道現場,最早出現在你頭腦里的作品想法是什么?
馬巖松:就是現在你看到的。我認識北川先生之前已經去過直島,當時就想,我要是能在這里建一座美術館就好了。我是建筑師,對環境比較敏感,如果很爛的環境我會抗拒它;如果很美,就會渴望通過作品和她對話。在任何地方,自然和藝術放在一起都很美好,我相信北川先生和大地藝術節要的也是這個。它背后也許還有政治、社會的訴求,至少這不是藝術的初衷。政治和社會的東西在建筑中卻很常見,因為任何建筑首先都要服務于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人,經常被認為實際用途強過精神性。但大地藝術給我的感覺是,怎么美好、怎么超現實,就應該怎么來。
這個隧道洞其實非常沉重,像個工程一樣,而且尺度特別大,有750米進深。當時主辦方給我打的第一個預防針就是“沒什么預算啊”,我心想這可怎么弄。那天我們走到隧道盡頭,在最后的洞口看到擺了很舊一張大桌子,那是個展臺,里面陳列了這個隧道的歷史;桌面上有塊玻璃,正好反射出洞口外面的部分景觀。我貼著玻璃拍了一張照片。現在那塊玻璃就變成了你所看到的整片水面,變成了“鏡池”。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水面”和“玻璃”當時能讓我聯系起來,有可能是人在隧道里聽見巖下流水嘩嘩的聲音,眼前卻干巴巴的是個水泥空間。直覺應該有這個水,然后想到通過反光,把內和外聯在一起。地上水面反射了完整的景觀,但完整還不足夠,我要洞外的一些變化,比如水波的流動被看到,要光線的變化更虛幻,然后就有了鋪滿內壁的不銹鋼板——有了反光以后,整個洞口邊緣變得有一點模糊,就有了一點幻覺。我追求的是,當有人走進洞里,區別于外部的另一種空間,那么就帶他走過這750米后,到達超現實。
三聯生活周刊:“超現實”是你的關鍵詞?
馬巖松:對,因為在隧道外面你已經看到水和山了,那不就是現實嗎?如果對自然沒有詩意的轉譯,那就還是現實。我做建筑也一樣,追求把現實抽離。我喜歡自然,它在有人類之前就存在了,對我來說就有一種遠古性。不管山、石,還是沙漠,我都追求把這些“遠古”跟特別未知的東西碰撞,把“熟悉”全部抽離干凈。當所有讓你感覺似曾相識的、能夠找到文化參照的東西都不存在了,你就好像掉進一個巨大黑洞里面,必須往很遠的地方去找坐標。我覺得人的想象空間就是這么來的。為什么我會被一些作品打動?因為它們把我帶到了一個不知何所在的地方,只能自己去感覺,去思想。
美術館對建筑師有種誘惑
三聯生活周刊:建筑和藝術最直接的交匯可以說是美術館(博物館),很多名建筑師也都希望留下一座自己的美術館建筑。在你看來,為什么美術館對于建筑師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馬巖松:美術館對所有想要創造的建筑師都有吸引力是因為,它是一種文化建筑。其他建筑,比如商業建筑、住宅,即使你對它有文化訴求也很難表達出來。但不管后面有沒有權力和資本,文化建筑要表達文化這是共識,那么建筑師他的思想、價值觀、他整個的歷史觀就都有機會表達出來,對建筑師絕對是巨大的魅力。我個人甚至覺得這是當建筑師的唯一誘惑:能把思想固定為歷史,被那么多人長時間地去感受、檢驗、喜歡或痛恨,這就是建筑師所擁有的滿足感。
三聯生活周刊:可以說說你個人最喜歡或最討厭的美術館?
馬巖松:我最喜歡丹麥的路易斯安娜現代美術館,很平實,跟環境結合得很好,也很美。談不上討厭(哪個美術館),但沒感覺的挺多的。我發現很多美術館就像宜家一樣,宜家就讓我覺得煩:特別大,很多人,進去了就出不來,然后功能好像特全,又有吃的又有買的。有很多專業人士把類似這種空間形式的美術館視為成功的美術館,但是如果這就是成功的,那一個美術館跟商場有什么區別?
在我看來,人們走進美術館之后應該在精神上有一種“放下”,而現在大部分美術館要的是現實,多少人、多少體量規模,造成它特別追求商場式的成功。我理想中的美術館要營造一個大的時空,讓人進去就能脫離——身邊的城市,平時生活里的那些東西,都能脫離掉。
三聯生活周刊:以上面說的這種標準,你覺得自己做的美術館達成了多少?我們知道你在鄂爾多斯有件作品。
馬巖松:我覺得鄂爾多斯博物館挺成功的,因為蓋完了里面什么都沒放(笑)。當時我受超現實的影響很強,覺得建筑就該超現實。鄂爾多斯這個地方本身就挺超現實。我第一次去的時候,新城還是個大模型,放在一個房子里,沙漠里唯一的房子,其他地方都空著,跟海市蜃樓一樣。我就想,如果這座城真建了,大模型變成城市了,我在沙漠里面弄點城市建筑算什么超現實呀,我應該把沙漠放回到城市里去,然后空降一個宇宙飛船。所以就做了一個像沙丘一樣起伏的廣場,上面放了一個金屬殼體。后來確實很多人愿意在那待著,在坡上坐啊、跑啊、騎車啊。那個空間讓人感到放松。四五年前我又去了一次,發現里面有展品了,中庭放了恐龍什么的,內容跟一般博物館也差不多,馬上就現實了。最近是在網上看到它幾張圖片,上頭那燈跟大紅燈籠似的,但那不是我的設計。
建筑是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關懷
三聯生活周刊:普利茲克建筑獎被視為全球建筑界的風向標。這兩年它的授獎對象,更多傾向于植根本土和嵌入社區民眾生活體系中的建筑師,有人形容為建筑的平民精神。你怎么看這種趨勢?
馬巖松:不,它仍舊還是一個精英的獎。我認為一年給一個人頒個獎,首先這種方式就是精英的,但是因為近幾年全球政治環境改變,一個精英的獎也要自我調整,要考慮如何在這樣一個政治環境中塑造新的精英。在過去,像扎哈、弗蘭克·蓋瑞、庫哈斯……他們都得過普利茲克,這幾個人的價值是因為他們的個性、他們的藝術性、他們的反主流。那個時代被人贊頌的品質在今天被認為是危險的,以及是一種不正確。現在是要更多考慮地域性,還有人的平等、文化的平等,比如對中國的關注、對南美的關注……對第三、第四世界的關注。
我覺得也不用太過于討論普利茲克會怎么樣,畢竟是私人基金會設立的獎。就是說不能把這個獎當成事業目標,因為它其實是非常現實的,是對這個時代的政治環境和文化環境非常敏感的……我曾經預言中國未來10年不可能再得獎,或者說我希望中國不要再得獎。當年中國獲獎(注:2012年度)符合西方對中國的城市化進行批判的需求,希望中國對城市化有一個反思,但不代表中國以后就不城市化了。中國未來的城市要怎么形成,這肯定是建筑師在未來十年二十年里要去直面的問題,而鄉村建設可能沒辦法解決中國城市這十幾億人口怎么弄。
如果說未來還是有一種普世價值的話,我覺得中國的建筑師會面臨這么一個挑戰:能不能在世界所有建筑成就之上往前推一步——這一步不僅是對中國的城市文明有益,也對西方發生影響。我覺得這才是最大的價值,不走這一步,就永遠是西方的好學生。
三聯生活周刊:說到未來,你好像不止一次提過建筑應該具有未來性。什么是你所理解的“未來性”?
馬巖松:建筑首先要解決問題,我說的“問題”是使用上的、社會的、政治的。人有夢想。所謂理想生活是什么?就是當下你還不在理想中,想要更好的,就是解決今天的問題。我相信建筑師都是精英的,是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關懷。不能說他空想了所以他就是獨裁者。包括古代文明,園林是大家商量出來的嗎?不是,它顯然是非常有造詣的少數人的想象。老北京城的規劃是大家投票,然后一起商量的嗎?肯定也不是,它背后的哲學思想和價值觀,是智者才有的高度……我們要相信這樣的人。不能說我不相信你,還要限制你,然后大家商量才是最好的,我覺得這種民主形式出不來好的東西,因為大部分人還是更關心眼前的現實而缺乏遠見。
三聯生活周刊:回到眼下這件隧道改造作品,你對它賦予了“未來性”的訴求嗎?你在創作過程中更多是建筑師的視角,還是藝術家的視角?
馬巖松:好像在這個作品里面我的身份更像藝術家。我總覺得人們對藝術家沒那么挑剔,對建筑師卻很苛求,人們會說這個建筑對我有什么用處,稍微跟實用主義不符,就被批評勞民傷財,同樣的人也會批評實用主義的城市是千城一面。談藝術的時候,多數人不會有這種心理,可能是因為藝術沒有花很多錢吧,或者藝術只服務人的精神性,在感受不到作品里面的精神性的時候,有人甚至還會自責,我是不是應該改造一下自己啊?但在建筑面前,尤其在公共建筑面前,態度會變得傲慢。我想這可能和建筑師的思想方式也有關系,一個建筑怎么讓它給所有人提供更寬容的感受?我喜歡的那些偉大的建筑師都是博愛的人,對這個世界很有愛,這也造成他們其實是悲劇人物,因為有太多美好的東西實現不了,但我個人覺得,他們的魅力也在于這種實現不了。(實習生王雯清對本文也有貢獻)
相關文章
- 中孚泰丨長春市規劃展覽館及博物館項目規劃展覽館布展
- HAS design and research建筑事務所作品|Simple Art美術館
- 簡美之境 山語銀城150平方米住宅設計
- HAS design and research建筑事務所作品|泰國鋁石窟文創場
- 殿堂級之作天橋藝術中心如何打磨?
-
王耀:滿足客戶的客戶需求 才是好作品

面對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建筑裝飾設計企業應該如何應對?作為設計院的領導,如何引導職場新人快速適應崗位
- 張展翼:平衡設計中的邏輯和非邏輯
- 劉亞濱:青春一路狂飆
- 設計師高媛:沒有完美的設計,都有不同的遺憾
- 優秀指導老師專訪 | 從選手到導師 周夢琪的“中裝杯”之路
- 中裝新網專訪 | 蔣燕微:用熱愛,譜寫設計的每個篇章
- 中外建姜靖波:深化設計未來也許更多是經驗和軟件的結合
- 鴻樣設計鄭惠心:創造多方共贏的互動空間
- 南通裝飾設計院秦嶺:成功的設計創意是實現得了的!
- 蔣繆奕:豪宅市場未來的發展方向
-
什么是設計師的成本與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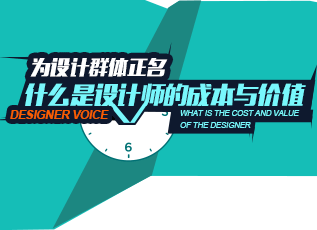
近日,《你個設計師有什么成本?》一文刷爆朋友圈,文中講了一個故事,表達了大眾對成本的理解,也提出了一個有
LINKS
中國室內設計與裝飾網 | designboom設計邦 | 新華網 | 中國建筑新聞網 | 搜房家居網 | 北京市建筑裝飾協會 | 中裝設計培訓 | 鳳凰家居 | 中國建筑與室內設計師網 | 中國網建設頻道 | 筑龍建筑設計網 | 視覺同盟 | 湖南室內設計師協會 | 城視窗 | 中裝協設計網 | 非常設計師網 | 新家優裝 | 行走吧,媒體團! | 新疆室內設計聯盟 | YANG設計集團 | 中式設計 | 大宅國際別墅裝修設計 | 四合茗苑中式裝修 | 設計王DesignWant?&?住宅美學Living&Design |





